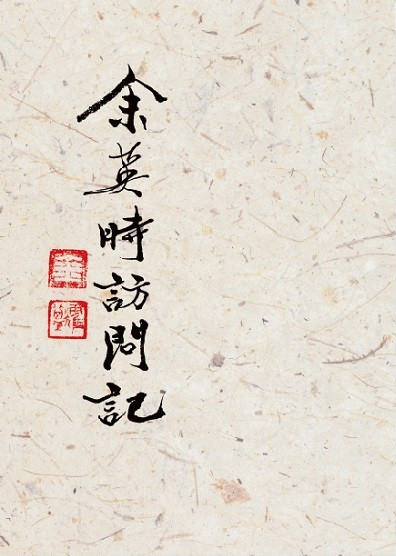
上圖:余英時訪問記(金耀基題字)
余英時訪問記──四海無家一滴淚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編按:張充和(1914年5月17日-2015年6月17日),祖籍安徽合肥,生於上海,作家、書法家。近代教育家張武齡之女,抗戰勝利後,在北京大學教授崑曲及書法,1949年1月赴美定居)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我們初次見面時,余先生專門推薦我讀一讀巫寧坤先生(編按:巫寧坤(1920年9月-2019年8月10日),江蘇揚州人,美籍華裔翻譯家,英美文學批評家。晚年有回憶錄《一滴淚》、散文集《孤琴》等)的《一滴淚》。恕我孤陋寡聞,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巫寧坤」的名字。告別時我從余先生家裡帶走《一滴淚》,在火車上一路看來,到了波士頓時,我打電話給余先生:「不知巫先生現在哪裡?如果有機會訪問他就好了。」「他現在就住在華盛頓。」2007年12月6日晚上,我坐在巫寧坤先生家裡,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插曲。
我將從余先生家帶來的《一滴淚》取出,請巫先生簽名,巫先生一看:「哎呀!這本書是我送給余先生的,扉頁上是我題的詩。」我嚇了一跳:這麼多天來我竟然誤以為那首詩是印在扉頁上的!我即刻向巫先生道歉,巫先生哈哈大笑:「沒有關係,這本由我寄回給余先生好了,我再送給你一本。」隨後便在贈我的那本書扉頁上題詩:「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還鄉半步橋。」當晚從巫先生家回來,我打電話給余先生,為書的事情道歉,余先生反而安慰我:「這是我的疏忽。」幾天後,巫先生用英文寫信告訴我,他和余先生在電話裡談起這件事,笑個不停。我彷彿聽見他們爽朗的笑聲。
在巫先生家,我發現他有一個特點:幾乎每講完一句話都會笑。而書桌上引人注目的是喬志高、巫寧坤、余英時3人並肩大笑的照片。我問起喬志高先生的近況,巫先生說:喬志高先生不喜歡華盛頓冬天的寒冷,已回到佛羅里達過冬去了。後來我在電話中向余先生請教喬志高先生的經歷與學問,喬志高先生原名高克毅,1912年生,為人豁達。「明年有機會再到美國,我一定要訪問高先生。」我對余先生說。話猶在耳,高先生2008年3月1日在佛羅里達逝世了。雖然高先生享高壽九十有六,真謂喜喪,但對我來說,無緣相見,不勝悵然。
巫寧坤的《一滴淚》中說:「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編按:李政道,江蘇蘇州人,生於上海,長於蘇州,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8年的故土了。」到了北京,在前門火車站接巫寧坤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
當年巫寧坤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將近舉手可得,卻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巫先生把自己的經歷總結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我勸巫先生把《一滴淚》之外的故事再多寫些。「我是懶得不得了的人。余先生叫我把這些文章集結在允晨出版,書名叫《孤琴》。」巫先生聽了哈哈大笑,「余先生讓我寫關於思想改造的歷史,他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所謂『心史』,特別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我最近發現最重要的作品是寫人的靈魂的受難。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寫的就是人的靈魂的受難。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那是最高級的人的靈魂的受難。《咆嘯山莊》寫的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所以才有價值,順著這個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則根本看不懂。」後來《孤琴》出版,也是由余先生作序。
余先生在《一滴淚》序中認為:「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序中也特別提到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趙蘿蕤(編按:趙蘿蕤,生於浙江省德清縣,女性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首位將英詩《荒原》漢譯為中文的譯者)這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以及她的先生陳夢家(編按:陳夢家,生於江蘇南京。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而飽受虐待,文革初期自殺身亡)。
提起陳夢家和趙蘿蕤夫婦,我馬上聯想到另一段記憶。我到上海訪問王勉先生時,談到錢鍾書(編按:錢鍾書(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江蘇無錫人,中國作家、文學研究家,古文學家錢基博之子。曉暢多種外文,包括英、法、德語,亦懂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在文學典故,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皆有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余光中分析當代中文時,稱道錢之西學列於中國人之第一流,夏志清說錢鍾書「才氣高,幽默,很會諷刺人。他什麽人都看不起,當時聯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雖然一方面仍是謙虛,但是恃才傲物。」錢鍾書去世後,學者余英時、王元化評價說:錢鍾書的離開標誌著出生於20世紀初的那一代學者的終結),王先生告訴我:「錢鍾書我只見過一次,在上海復興路,抗戰勝利以後我到上海,徐高阮帶我去。徐高阮說,錢先生請我們去吃點心,我們去了,談了3個鐘頭,無非品評臧否人物,陳夢家也在被罵之列。其實陳夢家早年以新詩人聞名,晚年致力古文字和歷史研究,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上海陸灝則說:「我是錢迷,錢鍾書迷,而非金錢迷。當年聽趙蘿蕤說她不喜歡錢鍾書,我很驚訝。可她確實說得乾脆俐落:『錢鍾書太刻薄,我不喜歡他!』」
後記──
余英時先生仙逝後,我的心情極為沉痛。起初1個月裡,我幾乎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黃進興先生(編按:余英時弟子,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副院長)和廖志峰(編按:允晨文化出版公司負責人)兄不斷寬慰我,使我心神漸安,追思這14年來和余先生的交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追思之中漸漸復活。我懷著溫情與敬意,重尋心史,文思忽如泉湧,於是日以繼夜,不計工拙地寫下余先生的言思。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當我全身心撰寫這部《余英時訪問記》時,彷彿余先生就在身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余先生的意趣形象永生在我的心間,付諸文字時,使我淡忘死別的痛苦,拋卻塵世的執念。因此,這部訪問記也是一部心靈史。
2007年,我和余先生初晤,是新聞記者對歷史學家的訪問。當年我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訪知識人」為理想,希望盡我所能,到處訪問名家,留下歷史初稿,給史家做材料,為事實找旁證。我和余先生一見如故,一席談勝讀十年書。第一晚餐敘時,我問余先生有沒有寫回憶錄的意願?余先生坦言並無此意。我們相談甚歡,片言即決,約定暢談成一本《余英時談話錄》。2008年,張充和女士人健筆健,欣然題寫了《余英時談話錄》書名。《余英時訪問記》成書時,則請余先生的摯友金耀基先生(編按:金耀基,台灣人,籍貫浙江天台縣,成長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研究興趣主要為中國現代化及傳統在社會、文化轉變中的角色,屢為台灣國民黨政府不願推行西方民主、禁止組黨辯護,與民主進步黨對壘,是保守陣營的知名學者)題寫書名。
《余英時談話錄》數易其稿,我寄回給余先生,希望由余先生親自校訂。當時余先生正忙於《論天人之際》的著述,無暇細改那本談話錄。等到余先生完成晚年學術巨著後,閒談中,我提到單德興先生訪問齊邦媛女士而促成《巨流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余先生何等智慧,當然知道我言外之意,這便有了《余英時回憶錄》。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序中說,回憶錄是建立在談話錄的基礎之上,那是余先生謙虛。實際上,我並無寸功。至多是我和余先生暢談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復活了余先生的記憶。對我而言,余先生樂意和我天南地北暢談,使我受益無窮。
這14年來,余先生對我殷殷寄語,最終形成文字的不及談話內容之萬一。而《余英時訪問記》的成書,得之於余先生者多,出之於我者少。從這個角度來講,《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都是余先生的著作,不過是余先生假我之手回顧他的平生學思歷程而已。
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余先生親撰回憶錄,遠勝我整理談話錄與撰寫訪問記的價值千萬倍。因此,《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以後,我萬分期待余先生親撰下冊,講述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以後更為廣闊的歷史世界。在我看來,余先生如能完成一部完整的回憶錄,重尋平生學思歷程,誠為現代文化史上重要的「心史」;則《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並無出版的必要。然而,如同我期待余先生晚年寫唐史著作一樣,此願成夢。唐代詩人祖詠〈終南望餘雪〉只作:「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而嘆「意盡」,留下無盡的悠思。余先生博大如海,如今的《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記錄的只是余先生世界裡的滄海一粟。
我天資不高,學識有限,但我以為志業生涯中最要緊的是敬業。如果能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更是仰不愧天。余先生能和我相談甚歡,也許正是欣賞我的敬業精神。我性格爽快,對余先生一向暢所欲言。而余先生提攜後輩不遺餘力,無微不至地關心我,使我如沐春風。這十四年來,余先生視我為忘年交,總是和我無話不談。因此,余先生對我的談話,便有了歷史價值。在余英時的歷史世界裡,我只是一個動了真情的提問者和聆聽者。
明代呂坤說:「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胡適先生對此言頗為欣賞,藉以教誨新聞記者。在我看來,新聞記者與歷史學家同樣擔負著為人辯冤白謗的道義。而余英時先生的著作中,常常為古今人物辯冤白謗,甚至多次為胡適先生辯冤白謗。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是余先生從事歷史研究的樂趣。余先生堅信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提倡做有尊嚴的知識人。「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是古今常態,胡適先生和余英時先生的生前身後,皆見此景。杜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已道盡底蘊。
在現代文化史上,有人和余英時同調,有人向余英時立異,但決沒有人能夠完全不理會余英時的學說。此意原論康德,余先生對此意頗為欣賞,先後藉以論韋伯與胡適。如今余先生隱入歷史,《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三部曲,成為余英時「心史」的一部分。余英時的歷史世界,如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期待更多朋友的共鳴。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上圖:余英時回憶錄
【文章出處】
《風傳媒》
〈余英時訪問記》四海無家一滴淚〉
2022-02-02
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4168196?mode=whole
作者:李懷宇
【作者簡介】
李懷宇,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記者,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
- Aug 01 Mon 2022 22:59
▲李懷宇:余英時訪問記----四海無家一滴淚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發表留言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