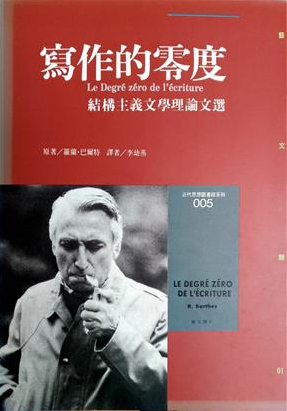
本書由三個獨立部分組成。《寫作的零度》相當於一份早期結構主義文學宣言,針對沙特「什麼是文學」的問題提出了擺脫激進文學傾向的中性文學觀,對法國存在主義和左翼文學提出了深刻的批評,顯著影響了其後西方當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新文學批評論文集》包含了作者對若干法國文學經典作品所作的細膩分析,被視為結構主義文學篇章分析的典範。 《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為作者就任法蘭兩學院講座教授典禮上的演講詞,相當於作者晚期文學思想的另一份宣言書。三部作品大致呈現了作者早、中、晚三個十期基本文學觀點的整體面貌。
《寫作的零度》導讀
羅蘭.巴爾特(1915—1980)是當代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法國結構主義人文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藝理論思想目前在歐美各國有著廣泛的影響。其文學活動涉及理論、批評與創作各個方面。在文學研究方面,巴爾特的工作是布朗肖、巴什拉等現代法國文學批評與理論傳統的繼續;就文學創作來說,巴爾特雖不是詩人、小說家或劇作家,卻是蒙田以來法國隨筆散文傳統的繼承者;此外,他還是法國現代派文學的一位頗具權威性的解釋者。作為六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五位主要角色之一的巴爾特(另外四位是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思想史哲學家福柯和馬克思學說研究者阿爾杜塞),儘管是法國當代新批評潮流的開創者之一,但他卻秉承了純粹法國的文學思考傳統。因此,我們不妨把他豐富多彩的文學生涯看作是今日法國文學精神新趨向的一個縮影。我迻譯這本選集的目的在於通過巴爾特的幾種代表性作品,使我國讀者了解巴爾特其人及其文學思想的一個概貌,以及了解當代西方文學生命的衰退和面臨的危機。
儘管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 19 世紀的法國出現過實證主義的科學式文學研究,但一般而言,法國研究者一直欠缺使文學研究系統化的興趣,這一點與毗鄰的德國形成對照。在德國近代文化史上始終存在著從哲學和科學兩種角度對歷史和文學進行系統的、概括的整理的傾向,其結果是,我們看到了各種附屬於哲學的文學美學(從康德、黑格爾直到現象學派)和今日德國甚為發達的「文學科學」。的確,沒有任何一位德、法哲學家能像柏格森那樣強烈地影響著現代法國文學家與批評家的思想,但是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人生觀和哲學觀方面,而不是文學研究的策略方面。法國與英國一樣有著豐富的「文論」傳統,主要表現為批評散文或隨筆的寫作,這類寫作與文學史著作一起構成了法國文學研究史的主流。
20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思想力式日益深入人心,歐美各國傳統上那種零敲碎打式的「文論」風格也發生了改變。首先英美兩國的「新批評派」思潮成為現代最有力的文學反省形態之一,從此「批評」發展為「理論」,文學研究的系統性、概括性、科學性都明顯增強。在英美「新批評派」崛起的二、三十年內,法國文學批評界並無類似的建樹。一方面存在著學院派的考據式和文學史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著法國的文論批評,如雷維里、梯包德、杜波等人的隨筆散文。二次大戰後,當薩特的存在主義籠罩著整個法國文化生活時,文學的反省變成了哲學的反省。薩特對法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正與柏格森的影響類似,這主要是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影響,文學研究本身性格的變化並不大。
20 世紀四十年代,當韋萊克企圖把歐洲大陸的現象學與結構主義文學研究方法同英美「新批評派」和「心理學派」的文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時,一門比較全面的文學理論或文學科學的建立似乎已經在望。四十年後的今日來看,韋萊克的名著《文學理論》與其說是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說是在文學反省急劇演變歷史上的一次暫時性總結。《文學理論》不是文學思考的結束,而是文學思考的新起點。結果五十年代以來不論在西方哪個國家裡,文學研究的內容和方式都在迅速改變之中,其中尤以法國的情況最為突出。
比較而言,法國的文論家更具有主觀的性格。「文論」往往成為借題發揮的手段,批評活動本身成為批評家「介入」文學(而不只是「觀察」文學)和生活的方式。當結構主義思潮取代了存在主義思潮之後,思想家的興趣似乎從關心和改變社會文化生活轉為對生活的冷靜、客觀的思考。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影響,似乎使結構主義更像是科學式的探討了。毋庸置疑,法國結構主義(包括文學結構主義)具有較強的科學性格,但與此同時它也具有哲學的和非科學的性格,對於文學結構主義思潮來說尤其如此。一般而論,法國文學結構主義是哲學、科學和法國批評傳統的綜合產物;或者說是法國研究者借助於各種知識手段對一些重要文學問題進行綜合性思考的產物。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思考既反映了現代西方文學研究的共同成果,又反映了法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傳統,巴爾特本人的文學活動集中體現了各種文學研究態度與方式的交互作用。
西方各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是一種歷史上的綜合研究,其中既包括歷史事件與人物傳記的記敘,又包括各種準科學式的考察。其中屬於科學研究的部分,逐漸分化為各種專科類型的研究,於是文學史、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語言學等均應運而生。儘管文學研究科學化的趨勢使文學現象的說明更準確、更富概括力,但人們逐漸認識到,科學式的研究往往是對文學作品的各種外部條件所做的因果式說明,文學作品本身的各種美學特質並不必然因此而使人獲得充分理解。至於韋萊克早年取自茵格頓的文學本體論觀念,仍然也是取自文學以外的哲學領域的,這類哲學式的文學思考,往往會失去許多文學本身固有的東西;同時,文學與人類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種聯繫,也並不由於科學式文學研究的進步而變得更為明顯。這種困惑的產生首先是由於文學實體本身的內涵還需作深入探討;其次,文學的理解似乎越來越有待於人類文化全面理解的提高。這大概就是後來文學解釋學廣為擴展的根源之一。正是由於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研究本身的困境,才傾向於對文學研究的內界與外界劃出更適當的區分線來。
在各種科學式的文學研究中語言學方法佔據特殊地位,這是由文學與語言的特定關係所決定的。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語言似乎自然地被劃入文學研究的「內界」了。不論是韻律學、風格學的研究,還是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文學性」探討,都突出著文學語言本身特點的重要性。結構主義以來的文學語言學研究與古典語言學研究完全不同,後者具有從歷史生活各方面進行外在的文學語言資料考證的性質。而由結構主義語言學發展而來的符號學卻進一步發展了文學語言形式面探討的趨勢。其結果導致了文學研究的重點從內容面轉到了形式面。法國的存在主義文學研究向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過渡就體現了從內容面向形式面的轉移。文學形式面研究的側重不僅輕忽了傳統的哲學式與歷史學式的文學研究,也輕忽了各種「外在的」文學科學式研究(包括韋萊克的各種研究方式)。結果,客觀的、全面的、系統的科學式文學探討在法國文學發展的新條件下減少了吸引力。
但是我們看到,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確表現出了另外一種系統化與精確化傾向,這個新特點反映於今日法國的「新詩學」之中。「新詩學」與文學科學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只關注文學形式面的系統考察,後者則兼顧到內容面或以內容面為主。但是「新詩學」並不等於法國文學結構主義,前者是一種純理論研究,後者則包括了各種其他的批評、描述與分析活動。正是在這種區別中我們看到了托多洛夫與巴爾特的差異。托多洛夫只是研究家,巴爾特首先是「文士」,其次才是研究家。如果我們的「文學理論」含義,大致指那些系統性的、概括性的研究,「文學批評」大致指那些零散的、具體性的考察;那麼可以說, 20 世紀的法國文學研究思想始終是在這兩個極端間搖擺,而巴爾特就是這種搖擺運動的突出代表之一。
巴爾特的確是一位當代法國文學理論家,因為他曾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般文化對象進行過十分系統的考察(如《符號學原理》、《時裝系統》),同時他又對具體文學作品進行過系統性的本文分析(如《S/Z》)。當我們說巴爾特是批評家時,也有幾層意思。首先,他對具體作品(如巴爾札克的《薩拉辛》)、人物(如對《茶花女》中女主人翁的分析)和作家(如拉辛)都作過許多評述。其次,他還對文學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在此意義上他又被稱作社會文化批評家。巴爾特發表的為數甚多的文學隨筆使他成為法國六十年代以來最負盛名的「批評家」。在巴爾特畢生的文學著述活動中同時表現出這兩種表面上看來有些對立的思考傾向:即系統整理和個別思索。這一對立既是現代科學精神和法國「文論」傳統之間對立的反映,又是當代法國文學思考內在張力的反映。因為對文學本身有豐富經驗和實踐的巴爾特始終認識到,系統化與理論化並非總是適當的,因此他寧肯時時在具體文學本文的「安全島」上休憩與深思,也許這就是巴爾特特有的文學符號學分析產生的緣由之一。
巴爾特由於撰寫了大量文筆優美、意蘊深邃的隨筆散文,而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學家或「文體學家」。青年時代的巴爾特懷有與馬拉美、紀德和加繆同樣的文學家心靈,他也曾為文學與人生使命這類大問題困擾過。然而他內心紀德式的恬淡很早就勝過了薩特式的熱情。法國現代派文藝的超脫與強烈的分析興趣雕塑出他這樣一位別具一格的文學家形象。同時,對語言本身深度的特殊敏感和銳利的意義剖析能力,又使他成為一種新文學形而上學實體——「寫作」(ecriture)論的提出者,從此開闢了文學形式主義研究的新途徑。巴爾特在科學與理論的呼聲越來越強大的時代,堅持表明散文批評有在系統理論之外獨立存在的必要;批評家不同於冷靜的科學分析家,他的身分毋寧是介於詩人、小說家與理論家之間,因此也就是廣義「作家」的一員。在這個問題上,巴爾特既不同於許多純文學理論家,又不同於正統的文學科學家。他的形式主義文學觀,強調文學研究對象不應是只有歷史學才能加以處理的「內容」,而是內容的條件,即形式。形式當然是傳達內容的意義的,但巴爾特認為這個意義是不斷改變的,並不存在科學家想要找出的那種始終不變的潛在意義。因此文學批評不是科學,科學研究意義問題,而批評只研究意義的產生方式。巴爾特倡導的文學形式主義立場在六十年代初曾遭到法國索邦大學學院派權威R﹒皮卡爾的激烈攻擊,結果爆發了1964年著名的「批評家論爭事件」。導火線是拉辛研究方法問題。皮卡爾是法國權威的研究拉辛的專家之一,他十分討厭巴爾特的形式主義拉辛研究。1965年皮卡爾更以《新批評還是新騙術》一書對巴爾特本人進行了人身攻擊,稱新批評「無知」、晦澀、狂妄、虛偽,同時重申好的批評家應是:博學、清晰、謙虛、真誠。巴爾特則從更高的角度指出,這場爭論反映了法國批評理論本身的危機,他強烈批評學院派盲信語義學、心理學、文體學等「科學方法」的弊病,宣稱一門文學的「元科學」並不成立,認為學院派想一勞永逸地發現文學本文意義的方法是無效的。這場論戰最終以學院派敗北而告終。
在文學形式的問題上,巴爾特區別了語言形式與寫作形式。語言是社會強制性系統,它對作家的規定是否定性的,它同作家在社會與藝術價值方面的選擇無關。「寫作」則是一種獨立的文化概念,儘管它具有語言的物質性、社會歷史性與身心方面的特性,但它是超出語言和心理的,或者說它是各種有關因素的交互作用場,它呈現出各種形式的特徵。一位作家除了歷史道德的選擇之外,還具有一種寫作形式或方式方面的選擇。不過,早期受過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巴爾特強調,寫作方式的承諾或選擇不是個人性的或心理性的,它是由經濟與歷史中各種客觀因素決定的。儘管巴爾特有關寫作方式(或文章形式)的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形式主義的文學研究,但巴爾特主要是一位「具體的」分析家,而不是理論概述者。巴爾特的寫作理論仍然是以隨筆散文的形式發表的。巴爾特的文學形式主義與其說是某種文學理論的完成,不如說是某種新研究方向的開始。
作為唯美主義文學家的巴爾特對西方物質主義不滿,他沉浸於寫作不僅是「為了使自己被人所愛」,同時也是為了逃脫各種現實苦惱。他曾指出,自己早年寫作與分析的最終目的在於揭示「資產階級價值體系總崩潰的各種象徵表現」。巴爾特早年對薩特、布萊希特、加繆的興趣,表明他本來也具有以作家之筆來干預生活的志趣;然而不久他就像加繆一樣採取了「不介入」態度。馬克思主義對他來說只成了理論分析工具之一。他的寫作於是變成「白色的了」,理論根據不再是內容上的道德原則,而是形式上的「道德原則」。巴爾特想指出當前西方文化與思想的病因,卻無意介入解決之途。這是巴爾特為自己一生所劃定的界域。值得注意的是,巴爾特的文學態度與選擇,加強了羅伯—格里葉以來各種非現實主義的法國文學創作方向,甚至影響了法國一代人的文藝思想。可以說,巴爾特的美學認識論的相對主義本身就集中地反映了今日西方文藝思想的危機。
這本文選希望把巴爾特這位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和文化批評家以及符號學家的面貌展現出來。由於巴爾特論著甚為豐富,本文選只能反映其文學思想的幾個側面,希望這個初步的介紹能引起我國研究者進一步探討的興趣。
1977年初在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上所作的這篇著名的《就職講演》,概述了巴爾特自己的基本文學觀點和設想,發表之後引起了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反響。我把這篇演講詞置於本書中,意在讓巴爾特本人直接向讀者談述一下自己的文學思想。
我也選擇了幾篇巴爾特的隨筆散文。關於紀德的一些片斷隨想可以讓我們了解巴爾特成為理論家之前的基本文學趣味。另外兩篇隨筆散文一短一長,可以介紹一下巴爾特特有的文化分析或批評的寫作風格。最後一篇「歷史的話語」是他對歷史學寫作形式結構分析的代表作,本文有助於讀者了解巴爾特的歷史哲學觀。巴爾特大量的隨筆散文今後應當有專門的譯文集加以介紹。
《寫作的零度》這個以語言學術語「零度」標名的著作是巴爾特的第一本書,實際上是一些文章的匯集,算是巴爾特形式主義文學觀的一份綱領性宣言。這時的巴爾特尚未受到語言學的正式洗禮,但他的語言觀已不期而然地接近於索緒爾的語言觀了。許多研究者都指出過,這本書中的主題已包含了他後來加以展開的大部分重要討論,如有關語言結構與寫作方式的關係、歷史與寫作方式的聯繫,思想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寫作方式的多重根源,寫作的效力等等。研究者指出,此書的動機之一是企圖間接地回答薩特在幾年前提出的「文學是什麼?」的問題。然而巴爾特這本處理所謂「自由與制約的辯證關係」的書提出了與薩特相反的或補充性的回答。在當時來說,巴爾特的文學形式觀是與流行的存在主義文學觀正相對立的。巴爾特認為薩特對自己的問題只提出了「外部的」回答,他卻要深入到文學內在的核心中去。後來巴爾特曾回憶此書付印前夕他在巴黎街頭獨自漫步時的緊張心情,那時他已意識到這本小書將會給法國文學研究帶來的深遠影響。對於我國讀者,這本書一方面可使我們瞭解,巴爾特是如何通過寫作形式的分析來解剖資產階級文學生命的內在危機的,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有關文學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的有用資料。
《符號學原理》最初發表於《通訊》期刊中,後來才發行單行本。這本小書很快使巴爾特贏得了當代文學符號學家的令名。一般來說,巴爾特是符號學概念與方法的應用家,而非純理論家,但是這本書由於論述整齊嚴密,簡潔明瞭,已成為當前西方文學符號學研究的必讀書和入門書了。由於今日西方符號學派別林立,內容紛繁,巴爾特這部「原理」並不能成為有關符號學各種理論的全面導論,然而它包含了目前西方文學符號學分析中所用的大部分概念和方法。無論在英美還是在法國,文學符號學都是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巴爾特的《符號學原理》對於研究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讀物。
最後我們選擇了今日美國和法國兩位著名的女文學理論家評述巴爾特思想的專論。蘇珊.桑塔格是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反解釋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所編選的《巴爾特文選》目前在美國大學裡很流行。《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爾特》即是她為該文撰寫的長篇導言,算是她對巴爾特逝世之後所作的一篇「蓋棺論定」。由於法國文學理論家往往用語抽象,文句晦澀,英美一般讀者習慣於通過英美研究者的解釋來理解法國人的思想。桑塔格這篇文章也寫得比較明白易懂,同時她所側重的是作為批評家的巴爾特,對於我們很有用處。本選集最後還選擇了當今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和符號學家克莉思蒂娃在七十年代初寫的一篇專論「人怎樣對文學說話」。當時巴爾特的結構主義思想正在(包括克莉思蒂娃在內的)所謂「後結構主義」影響下開始轉變。克莉思蒂娃這篇長論更能從哲學和文學理論角度闡釋巴爾特的寫作觀,但用語也更抽象難懂一些。兩篇文章配合起來讀,就可從不同方面幫助我們了解巴爾特的文學觀;同時也可展示美、法兩國不同的文學研究風格(對同一人物和同一主題的不同論述態度和方式)。
最後談一下本選集中名詞翻譯的問題。六十年代以來由於人文科學領域內跨學科研究傾向和抽象性不斷增加,有關術語名詞漢譯問題較前更為困難,其中尤以法國的文學理論為甚。本書的處理與我在其他有關著述中的處理相同,主要依賴同一名詞在不同語境中的普適性,而不是譯名含義的絕對貼切,因為目前這是很難做到的。原因不僅在於中西語言本身語義結構的差異性,更主要的在於我們對當代西方人文科學知識的接觸還不夠深廣,現成的漢語名詞還未經過大量的詞義結構的擴大調整。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展開,中西語言詞義對應的程度當會逐漸增加。因此我們希望讀者多從上下文中去領悟一些專有名詞的含義,而不要按漢字通常的詞義幅度來把握它們(如「寫作」這個詞就與漢語中該詞通常的含義很不相同)。本書譯文中的錯誤與不妥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指正。本選集中各篇除《歷史的話語》譯出於1979年外,其他都是今年譯出的。各篇原文出處請見各篇譯注。
1985年11月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